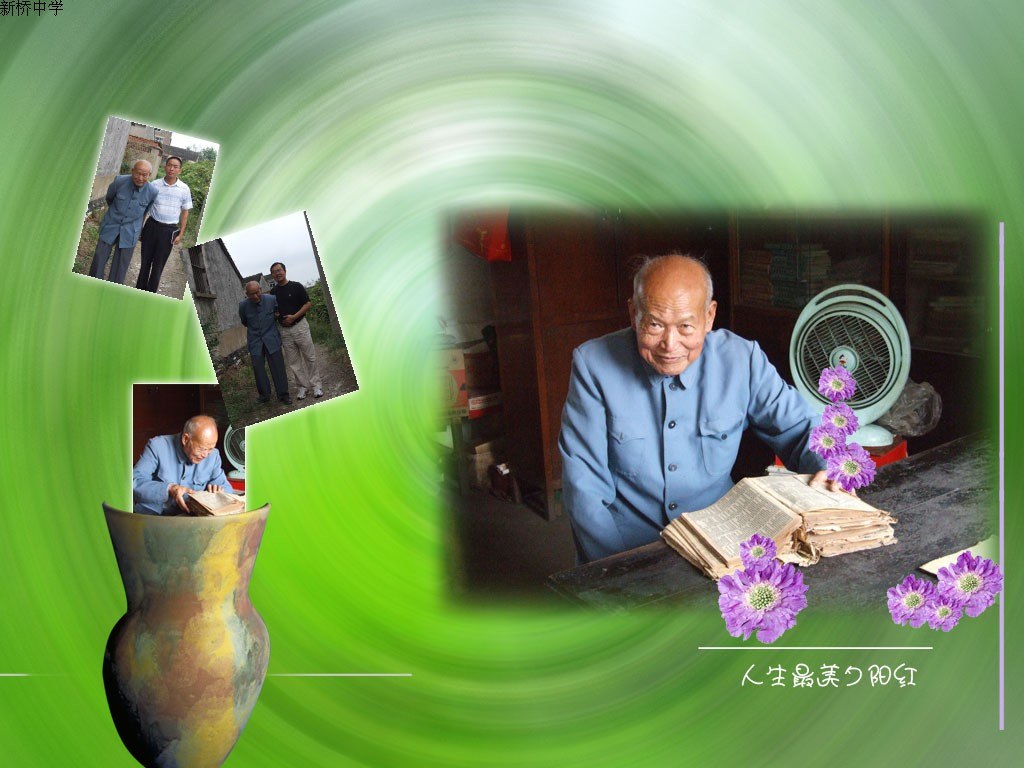人生最美夕阳红
——访原常州武进政协委员、新桥中学离休教师黄远
在位于龙城北郊的潘墅古街上,当夕阳下,金色的余晖洒落归途的时候,人们总会看见一位耄耋老人,他白发稀疏、身躯佝偻、步履蹒跚……一双手却有力地挥动着一把笤帚,一下一下地扫着坑洼不平的青石街道,从古街的这头扫到那头,寒来暑往,一年又一年,风雨无阻,早已成了人们心中最美的风景!这位老人便是原武进政协委员、常州新桥中学离休教师、现已86岁高龄的黄远老师。
穿过潘墅古街的一条小巷,再走过一段铺满野草的乡间土路,便到了黄远老师如今蛰居的院落。院子陈旧简朴,两间平房,青砖黑瓦,水泥院坝,院坝边的几丛夜夜红,星星点点的花儿色彩艳丽,暗香缕缕。客厅跟一般农家并无两样,一张八仙桌,两条木凳,如此而已。客厅正中斑驳的墙壁上,依次张贴着四样物事:一张离休证书,一副对联,一首律诗,一块挂钟。
离休证书镶嵌在匾额里,当年绸布做的大红花毫不褪色,点缀在匾额的四周,一片绸质叶片翠绿欲滴,竟无一丝尘埃,可见主人对此心爱之至。离休证书的落款单位为武进县小新桥中学,即常州市新桥中学的前身;落款日期为一九八九年八月,距今整整二十年了。黄远老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就参加了工作,从事教育41年。他于1949年被保送到位于无锡的苏南文教学院就读,早年供职于上海奉贤中学,当时奉贤中学隶属于苏南文教局,局长由苏南区党委书记和苏南军区政委陈丕显同志兼任。1976年他调入常州武进小新桥中学,那一年,黄远老师记忆深刻,如今回想起来,还泪光闪闪,他哽咽着说:“毛主席,周总理,朱德委员长就是在那一年与世长辞的……”在小新桥中学的日子里,黄远老师一直是教学骨干,担任语文教研组长。那时,学校没有图书馆,课外书籍很少,学生阅读量有限,视野狭窄,因此在每天早读课时,黄远老师便在黑板上写一些诗句让学生抄录背诵,并且他每每读到好的文章,便立刻用钢板蜡纸刻写油印出来给学生看,丰富学生的涵养。为了让学生才高八斗,自己得学富五车,黄老师酷爱读书写作,当年工资的相当一部分变成了书费和投稿的邮资,晚年也不减当年,发表文章近百篇。今天,在他狭小的老屋居处却有一间小有规模的书屋:一张宽大的写字桌,被岁月磨蹭得光滑发亮,上面排放着文房四宝,砚里墨汁未干;一把藤椅,一张木制椅,一张竹制躺椅,黯淡无色;三个木质书橱,高矮不一,都装满了藏书,有《郭沫若全集》文学编和历史编,每一类型多达17集,有《官场现形记》、《老残游记》、《镜花缘》……一本辞海,厚厚的,破败不堪,线条脱落,蓬松地放在书厨顶部,捧在手上,轻飘飘的,重量与体积极不匹配,时间已剥去了它的重量,但份量不减;还有一些字帖,包括王羲之的,整齐地叠放在位于屋角的他母亲的梳妆台上,散发着久远的气息。
黄远老师具有前瞻性的教育思想,针对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极端摒弃传统教育的改革呼声,他在1986年第11期的《语文教研》杂志上发表了题为《语文传统教学并非一无是处》的文章,强调在传统中创新,既需要“启发式”,也需要“注入式”,提倡培养创造型人才。文章发表在杂志的首页,当时引起了较大反响,如果以今天新课程改革的眼光和思维来重新审视,黄老师的观点也正迎合当前课改潮流,可见当时已过离休年龄的他对教育的痴情、执着与反思。由于学校工作的需要,直到年近古稀,黄远老师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了一方杏坛热土,一生桃李满天下。在他的班级里,曾经创下了50多人全部考上大学的奇迹,其中一个弟子,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,现在中国地震局任要职,去年汶川地震期间接受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,两鬓斑白的黄老师从电视上目睹此情此景,心中自豪感难以抑止。他曾经在《解放日报》发表散文诗《春蚕篇》,从中可见他对教师这个职业的自爱自敬:“蚕儿眠了。一个个昂起头,默默地,不食不动。眠一次,便要蜕皮一次。它们在努力地突破‘旧我’,以得新的成长。它们是在经历着一场艰苦的自我斗争呵!它们不辜负主人的辛勤饲养,它们遍体发亮,一个个从容地而又紧张地在吐丝结茧了。它们毫无保留地献出了自己的一切。‘春蚕到死丝方尽’,便是诗人对它们这种精神的热情礼赞!”
黄远老师不是党员,但是早在学生时期他就受到党组织的影响,并于1948年参加了地下工作。在武进县圩塘黄家巷小学读书的时候,他喜欢读郭沫若的诗歌,深受感染,再加上新四军经常到学校来进行爱国思想宣传,初步具有了革命的思想基础。黄老师记得很清楚,读初二那年,自己参加了在西石桥召开的“五四”运动纪念大会,新四军51团团长张海荆在会上讲话,号召大家赶走倭寇,建设家园!参加会议的有农抗会、青抗会、妇抗会和群众等2万人左右,大家同仇敌忾,共唱抗日歌曲《八百壮士》:“中国不会亡!中国不会亡……”
初中毕业后,黄远老师考入常州群英中学,校址在瞿家祠堂,即现在的觅渡桥小学。他亲眼目睹了国民党腐败统治下的百姓三餐不饱,衣衫褴褛,拖儿带女四方逃荒的惨象,便经常撰文抨击,引起了地下党的注意,后来加入地下党的宣传队。宣传队分为刻字组、印刷组、运送组、发放组,每组四五人,严格保密,连家人也不知情。黄老师参加的是发放组,负责传单的发放,每到夜里,尤其是云黑月淡之夜,就是黄老师他们活动的最佳时机,大家分头行动,猫着腰,静悄悄地把传单放在弄堂居民门口,并用小石子压住,以防被风吹走。有时碰上国民党的巡逻队,黄老师灵机一动,或者把传单塞入裤裆里,或者丢进运河里,多次化险为夷。
晚年的黄老师淡薄明志,宁静致远,心境宛如堂上那副对联:“好山入座清如洗,嘉树当窗翠欲流。”读书、写字、看报、散步是他生活的主要内容,乐善好施是他品格的自然流露。离休二十年来,他不但每天打扫着那条古街,而且每年春节,自费买来红纸,写好春联,给小街上的每一户居民和店家送去。按规定,他离休后应该享受副县级待遇,医药费和护理费全部报销,与他同级别的人有的因此每年报销十几万,可他总是分文不多取。回头再看墙上的那首由常州书法协会徐浩然题写的律诗,其实是他人生的真实写照:
闲来无事不从容,睡觉东窗日已红。
万物静观皆自得,四时佳兴与人同。
道通天地有形外,思入风云变态中。
富贵不淫贫贱乐,男儿到此是豪雄。